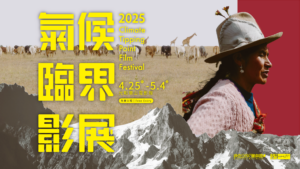(烏拉山變形記 劇照)
本次「核電影」影展中,在同一場次聯映的《烏拉山變形記》、《核廢人生》,是兩部影像風格、主題都相當特殊的電影。
看《烏拉山變形記》的時候,我一直想到零核時代展出的《世界被曝者攝影展》中的一張照片:哈薩克塞米巴金斯克州的一個小農村,被蘇聯軍方當成核武試爆場所,該村村民們甚至被迫留在村內不准遷移,因為軍方想要藉由他們的身體變化,觀察核武對人體的影響程度。他們的餘生就是活生生的人體試驗品。
同樣的慘劇,早在1957年九月,就發生在位在歐亞邊境、烏拉山區切利亞賓斯克(Chelyabinsk)的瑪雅克科技生產區(Mayak Scientific-Production Association)。這是一個複合式的核武產製區,1957年由於核廢料處理不當,發生爆炸,據說當時有約一千平方公里(十萬公頃)的土地受到高量輻射汙染,受低度污染地區更高達23,000 平方公里,約台灣的三分之二大,且死傷人數仍然是個謎。
然而因為核武屬於國防機密,蘇聯當局一直防堵消息走漏,以至於一直到1989年之後,這個事件才逐漸為人所知,但相關資訊至今還是相當有限。

(攝影:侯希婷)
「看到這部片很驚訝,以前完全沒有聽說過烏拉山核災的故事,看了電影才曉得這場災難的影響和傷害,並不亞於大家所熟知的車諾比核災。」詩人、導演鴻鴻在映後座談中說。
片中荒蕪、淒涼的山村景象,遺世獨立、淳樸脫俗,有時美的令人屏息,但是當輻射偵測器開始尖叫後,銀幕前的人們才猛然驚覺這個地方曾經的核殤記憶。
《核廢人生》則是一部荒謬中見人性的劇情短片,導演來自烏克蘭基輔。在同一個核廢料處理場工作的夫妻,每天在生產線的兩端從事不同的工作,開著卡車運送物資、或者清洗受到輻射的工作裝束。
「在這種單調無聊、冰冷的生活節奏中,不時有人性被科技扭曲的荒謬感,但是即便如此,片中的主角仍舊有生養下一代的渴望」鴻鴻說。
兩部片,一部黑白、一部彩色,一部是紀錄片,一部是劇情短片,相同點是對白都極少(核廢人生甚至毫無對白),純粹藉由影像語言,展開對於科技、災難與文明的循環辯證,以及人在歷劫之後的強韌生命力,也讓我們看到較為少見的亞洲一角。

(核廢人生 劇照)
觀眾中有一位曾到烏拉山地區留學(當地幅員廣大,並非在核災地居住)的女生,特別來觀看這場放映,說起自己的經驗:「當時我的同學中有來自車諾比地區的人,他就有六根手指頭;也有認識的學長來自烏拉山地區,身體都有一些慢性病狀。」
到場觀影的立法委員尤美女說:「看完片子,即便知道背景有可怕的輻射,但烏拉山區的民眾仿佛仍在日常生活中安然自得。這些影像會不會反而削弱反核力量?畢竟很多人從表面上看到沒有什麼大危險,就不會那麼反核了。」
綠盟理事長賴偉傑回應說,其實就像是日本政府在災後不斷修正人體可以承受的輻射值上限,就是為了要讓社會在表面上回復「正常運作」。而這些「看不見」,往往一點一滴侵蝕改變的動力。我們真的能夠假裝若無其事嗎?
也到現場觀賞電影的紀錄片導演柯金源則補充,其實過去在桃園龍潭的中科院核武研發基地,同樣曾經發生過核輻射廢水外泄的狀況,但也由於是國防機密,而罕為人知。
鴻鴻最後說:「不管怎樣,大家還是一起努力反核吧!不反核不行!」即便「核電影」影展並不刻意凸顯「反核」立場,但在銀幕上目睹各種人類在「核」之下的生存處境後,這句話幾乎變成每一位參與映後座談來賓的共同心聲。
這兩部電影的影像震撼力,都是用文字難以傳達的。本週六(11/30)在松山文文創園區還有一個場次,快來看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