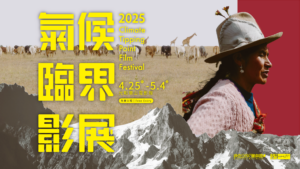紀念前蘇聯核災之後的紀實故事書《車諾比的悲鳴》,第一個故事的第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我不知道應該說哪個故事?──關於死亡或者愛情?也許兩者是一樣的?我該說哪一種?」然後她真真切切地說了一個以死亡為序曲的愛情故事,從她新婚的消防員丈夫出門去救(當時她們還不知道是)核電廠的火,那一夜,開始說起。
撇除了「核爆」這個主題,《核爆青春》就是一個浪漫感人的青春愛情故事,應邀出席本片座談的導演葉天倫也在座談的一開場就先指出了這一點:《核爆青春》首先是一個愛情故事,而在電影與文學的領域當中,愛情始終都是一個具有深厚傳統的描繪主題,愛情會遭逢困難、而一則動人愛情的可以故事之處,就是在於它會遭逢困難,戀人們可能遭逢天災巨變、可能遭逢戰爭橫逆,在變故當中誤會發生、戀人分離,愛情可能被考驗、也有可能被彰顯,而在這些起伏跌宕之中我們會被牽動、觸動,我們也在心中演練一遍自己所經歷的、所揣想與嚮往的愛情的形狀。但這部片以兩個校園青少年愛情萌生的時刻作為故事的基礎,卻又直接給出一個不可回復的、和其他任何災難都不相同也都不能比擬的「客觀困境」作為這場愛情的考驗元素──核災發生。在一個最淺白的層次上,我們就至少能從旁觀這對愛侶的過程裡面感受到了核災做唯一個環境障礙的特殊性:所有的災難都會過去,天災地變,我們會從災後復原、修補關係;戰爭也會結束,我們也能從廢墟當中生還,然後建造新的人生。但核災不是,核災沒有災後,一切的毀壞、人性的考驗,都從那個「災後」的時光裡,才算展開。男女主角所經歷的愛情的考驗,於是就也並非是災難使人分離、誤會使人猜忌,而更是「核災之後如何擁抱」,影片中呈現核災之後的歧視,作為「被污染人」而可能不再具有愛的權利,因為妳,這個人,本身可能已經是一個污染物了。

(攝影:侯希婷)
這是一部由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但同時作為一部討論核能傷害的電影,這部作品也在許多細節當中以非常細膩而婉轉的方式,展現了它的溫暖與仁慈,葉天倫導演舉例:災難從來都是不可預測,這是我們在閱讀一個災難作品的時候總是會有的常識,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部災難電影,因此劇中人物的每一次擁抱、每一次早晨上學、工作離家、每一聲尋常的再見,都有可能就是訣別。電影中核災發生那個早晨女主角與母親的爭吵,但導演溫暖得願意讓她們在分別/訣別之前即時和解、即時擁抱;而從符號論述的角度觀之,這部電影也讓許多故事細小的轉折發生在光明與黑暗、給電與停電之間,比方說男女主角初次獨處的泳池邊、小混混闖進男主角家與男主角爭開/關音響電器,比方說當男女主角災後重逢,男生的父親出現而發生的那個無預警、片中也沒有解釋原因的短暫斷電,這些在在都在與觀眾/讀者討論我們日常生活對於「電」的需要與使用習慣。片中少年們對於核災知識的熟稔與朗朗上口,還有在災難之中導演為我們演練與呈現的:官方的資料如何不可盡信,或者當學校老師作為權為、支配資訊與知識的人,學生與他們──彷彿也就如同我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些其實都是發人深省的。
座談主持人崔愫欣也提供了自己的觀點與經驗,她說曾經於金山核一廠附近的學校老師以核災、防災為主題進行座談,現場當她詢問老師、校長們有沒有聽過核災警報的聲響?當核災真的發生之時,是否有把握可以辨認?現場的師長們全都靜默無聲,而這個靜默其實也就凸顯了我們平日所能獲取資訊的片段──如果我們實際上連核災的警報聲響都不認得,我們如何相信政府口口聲聲告訴我們這一切沒有問題而且不會發生?葉天倫導演也隨即做出回應:電影之中的第一個死亡(女主角弟弟的死亡)並不是直接因為核災所致,而是一個意外。而這也就是一個再清楚也不過的訊號:意外會發生,這就是人間,無論我們認為意外的可能性有多麼地微小,我們都會知道,意外是會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