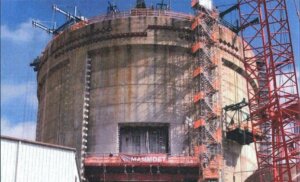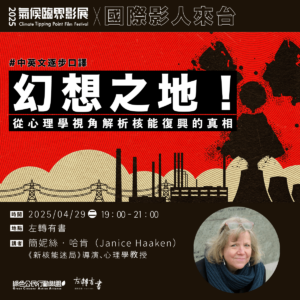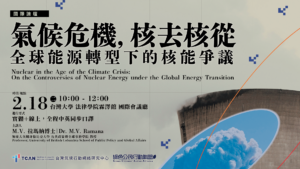《冰川回聲》是一部融合科學、文學與私人記憶的紀錄片。從童年與祖父母的傳統朝聖路,到如今眼前逐漸崩塌的瓦特納冰川,導演拍攝安德里與兒子一同凝視這片正在消逝的壯麗世界,也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愛與遺產的意義。
片中有句令人難忘的話:「氣候變遷這麼大的一個題目,我們需要科學,但是我們也需要神話,我們需要看一下過去,也需要未來,我們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 」
在7月20日,我們所舉辦的《冰川回聲》特映會於光點華山圓滿落幕。這場特映會邀請到了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洪廣冀,帶領觀眾從冰島的冰川談到台灣的山林,思考於我們周遭正在發生、卻常被忽視的環境變化。
關於氣候變遷,我們不僅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主持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分享自己非常被觸動,心裡有一個很大的震撼,它可以用這麼詩意然後很美的方式,去呈現極端氣候這麼巨大、有時候會覺得很沉重很無力的題材。對於片中那一位作家所說的,「氣候變遷這麼大的一個題目,我們需要科學,但是我們也需要神話,我們需要看一下過去,也需要未來,我們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覺得這段話非常的有共鳴。
冰川是我們眼中的遠方,是冰島人的日常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廣冀則回憶,過去對冰島的冰河地景感到遙遠而抽象,即便知道那裡正發生劇烈變化,也難以產生情感連結。然而,今年因為看了冰島藝術家Olafur Eliasson 的個展《你的好奇旅程》,產生了不同的體會。在他的展覽中至少就有好幾個關於冰川的作品,其中有一組冰河二十年間的照片,呈現冰島冰河快速退卻的事實,而這個退卻的過程已經是能在人的一生中被察覺到的;另一件作品〈冰河的最後七天〉,從一塊海邊撿到的冰河碎片開始,透過3D建模和水晶球,展示記錄冰塊消融與融水累積的過程,讓人直觀感受到氣候變遷的速度與重量。
透過故事重新建立連結,透過藝術改變我們的認知
對我們來說,冰川消失可能是很遙遠很陌生的事情,但對於冰島人來說,冰川消失是一種很切身的感受,不管是這部片還是Eliasson 的個展,都可以看到冰川與冰島人的生命經驗密不可分,冰川既是冰島人「需要對抗的自然」,也是一個永恆的、顯著的,承載了家族間記憶的重要地景,而藝術和故事作為這種情感的媒介是非常重要的,以故事來說,故事可以被一直傳誦下去、被反覆訴說,而且可以激起人類的感動與想法,透過故事,可以重新去建立人跟自然跟冰川跟很多很多東西之間連結;而藝術則是用來改變人的感知,改變人認識環境的方式,兩位作者就是這樣透過故事和藝術的方式,把冰河這樣一個很遙遠的東西拉到我們的面前,我們都知道有氣候變遷,我們都知道氣溫在上升,這是我們所知的知識,也是我們在有限的生命當中能夠察覺到的變化,但要透過故事,要透過藝術,要透過詩,要透過不停的訴說這一件事情,我們才會體會到,冰川這樣一個美的、壯麗的東西如果消逝了,是非常惋惜的,我們才會理解這是一個現實。
我們傳遞了事實,但也失掉了人與人、人與土地的連結
當討論到了「科學以外的生命經驗和體驗」時,洪教授表示,因為研究的需要和興趣,自己有去看一些日本人蒐集的台灣原住民傳說集,像是泰雅族和布農族對於大洪水的傳說、或是青蛙變癩蛤蟆、紅嘴黑鵯取火等等故事,在原住民的傳說當中,就有許多關於起源、關於環境變遷的故事,這些題材對台灣人來說,這些可能比「冰川」還要更親切,這些傳說或者說神話故事,其實不一定是口述史或是反應某種事實,而是在透過不停的傳頌「故事」,來建立人際之間、長輩和晚輩之間、人和土地之間的連結,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記錄某些事情,而是為了要建立和想像各種連結,這種連結比起在課堂上單純敘述西元幾年發生了什麼事,還要更能夠引起共鳴,在過往的課堂教學中,對於故事傳頌其實是非常欠缺的,也許我們傳遞了事實,但我們也失掉了連結,失掉了跟人和非人產生連結的媒介。
2100年有多長?比人的一生還要長,比愛和記憶更短
現場觀眾分享,自己對於這部片是很有體會的,比如像愛呀、連結呀,就會讓我想到,氣候變遷對現在的我來說可能沒感覺,或者2100年後我也沒感覺,因為我已經死掉了,可是這件事其實會影響到我的小孩,或我小孩的小孩,這樣的延續就會讓我意識到,這件事是有意義的,可是這個感觸結束之後,就會開始思考這部片想要觀眾帶走什麼?
消失的麻雀、消失的山間霧氣、消失的河川
老師回應,這部片子當中,透過作者阿嬤留下的幻燈片,還有透過和現實的對照,其實一直在傳達,我們的週遭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於冰島人來說,冰川是週遭日常的事物,那我們台灣這邊,大概只有冰河的遺跡,就是我們有雪山和南湖,所以可以看到台灣過去在冰河期的時候,這些從北極圈下來的冰川把台灣的山挖出了大洞,以雪山為例,從黑森林出來,就可以看到一個大碗公直接在你面前這樣展開,從旁邊爬上山去,就可以上到雪山主峰;南湖那邊也一樣,過了五岩峰之後也會看到一個大碗公,在碗公底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冰河挖過的痕跡。
我要說的是,我們這邊當然沒有冰河,這些東西當然不是我們日常的事物,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其實有一些感覺最日常的東西,可能是在我們有生之年,在我們過去的幾十年間就已經慢慢沒有了,比如說麻雀這種鳥,在我小時候是很常見的,是都市裡最常見的鳥,我現在將近五十歲了,我就發現現在走到外面很少看到麻雀,都找不到麻雀,現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八哥或是其他的鳥,與此同時,我也想到自己在唸森林系的時候,我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解說員,所以我一個月要有幾次去小油坑還有去擎天崗的遊客中心,騎摩托車上去的時候,就會感覺到這兩個地方常常都是滿滿的霧,很冷很濕,當時在遊客中心最常感覺到的,就是這些觀光客爬下山之後,都會跑到遊客中心說好冷、問有沒有熱水,但現在去陽明山,會發現這種濕冷多霧的環境,幾乎已經沒有了。
面對氣候變遷,我們可以做的,是從週遭的變化開始關注環境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這部片想要觀眾帶走什麼?冰島人有冰島人他們要去關心的點,而這一個點會連結到更大尺度的全球變遷,但是對於幾千幾百年這種很大的尺度,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我們可以做的,真的就是從週遭著手,有時候週遭環境的變化,反而是我們最沒有辦法意識到的,我們可能會注意到格陵蘭的冰川崩落,卻對於麻雀今年已經慢慢消失這件事沒有感覺,對於霧慢慢沒有了也沒有感覺,或者說對於我們的河沒有水了,也沒有感覺,所以說面對氣候變遷,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就是回到我們的週遭,我們會覺得冰川看起來新奇、很壯麗、很不一樣,但對於冰島人來說,那就是他們的鄰居,就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東西,冰川之於冰島人,就相當於陽明山的箭竹林或是常綠闊葉林之於我們一樣,這些就是我們週遭的環境,我們也同樣經歷了週遭環境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我們需要去注意到、觀察到,再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把這些東西留下來,這些東西可能會是各式各樣的故事,然後衍生出各式各樣對於環境、對於過去和未來的想像。
環境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如何影響環境?
主持人陳詩婷也回應,在選片的過程中,有發現到這部片其實是以一種個人生命經驗的方式在談,所以觀看這部片時,也感覺到它在召喚自己的生命經驗,但不是對於冰川,而是對於自然環境改變的鄉愁與悼念。我從小是在農村長大,然後旁邊都是田,後面還有竹林,田旁邊的圳溝是有魚跟蝦子的,但這些東西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就消失了,全部都蓋了違章工廠,一直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我才發現當時的自己是很悲痛的,這個悲痛不只是因為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沒有了,更是在於以後我愛的人、我在乎的晚輩們,他們看不到這些東西,他們沒有辦法在這一片樂土上面長大,這個心情很直接地促使我去做現在在做的環境運動的工作,所以我想,每個人在看這部片的時候,也許也會勾起生命經驗中某個很重要的印記,那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些改變、怎麼促使我們對這個社會發揮影響力?我期待也相信這部片可以給每個人一些這樣子的提問。
核廢料的時間尺度,遠超過人類語言所能表達且理解的尺度
觀眾之一的江櫻梅老師發言,自己是第二次看這部片子,雖然有買了書,但很喜歡這部片子裡的旁白,文學性很強,比書還要更濃烈。對於片子裡說的「超過人類語言所表達的且能理解的尺度」,就讓我聯想到,核廢料的時間尺度,也不是人類的時間尺度,所以向其他人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很多人都是無感的。片子裡面談到的故事,比如個人家族的故事,或者說北歐那邊有很多豐富的神話故事,但我自己是威權教育中長大的,所以我所知道的神話,是威權教育下有一點模糊的中國的神話,可是那不是我們這個地方長出來的,我在這一二十年也斷斷續續聽了一些原住民的神話,各個原住民的神話就是從台灣的山川土地裡面長出來的東西,現在有蠻多的出版書籍、繪本、或是一些部落的中學會有這樣的教育,我會覺得原住民文化教育不是只適合在部落的學校,也可以出現在都市的學校、非原住民的學校,讓更多的台灣人,無論是何時移民過來的人,都能多知道從這片土地長出來的神話,可是現在小學中學的時數有限,各種學科都在搶時間,小孩的書包也沒有因此變得比較輕,如果有一天教育部長規定,全臺小學都要實施原住民教育,那樣好像又是另一個問題,所以我想到的就是,怎麼樣從教育者身上自己長出這樣的視野?那麼他就會想方設法在最恰當的時間利用進去,或者是像洪老師說的,從博物館的展覽,從黑潮、季風、颱風三個很大的自然的項目,讓我們認識台灣之所以台灣,不是從上而下,不是從教育從官方,而是很多地方很多人一起努力,來長出我們台灣人看台灣的方式,那麼對我們的土地,就會比較有神聖感,如果我今天是個綠能業者,看待事物就不會只有從利益出發。
神話故事是一把雙面刃,屬於台灣人的故事未完待續
洪老師提出反思與回饋,原住民有非常多的創世神話,對於移居者來說,我們有沒有相對應的,關於過去、關於人與環境的東西?我覺得一定有,只是面對現在的狀況,各位可能也能體會到,神話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權力施展的工具,比如像我們這一代是威權體制的尾巴,所以我們當時最重要的神話,可能就是在河川裡面看小魚,在片中的故事,是源自於北歐傳下來的神話,但在台灣,情況可能會更複雜一點,這也許是我們要去認清的現實,台灣的故事除了有國家施加的東西,還加入了各式各樣移民四面八方混合在一起,所以台灣的故事會呈現出更複雜的樣貌,我也會覺得神話是個雙面刃,一方面它會刺激人們最多的熱情,刺激我們各式各樣的想像,與此同時,這些熱情與想像也非常容易被引導、操弄,容易被引導去完成某個正式的目的,包括原住民的神話,也可能會成為引導或操弄的工具,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樣去思考,是否能找到一種原汁原味、單純的故事?我個人是覺得沒有,所有這些東西一定都是鑲嵌在某種特定的政治或文化背景下面,因為神話容易被傳誦、被記憶、容易激發我們的想像及熱情,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有他的建國神話,這些起源的故事,即便是在現代國家,常常也是以神話的方式表現,我們如何去欣賞和傳頌這些神話,而不會讓神話在這個過程中變成操弄的工具?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好的環境教育不是說教,而是能帶來樂趣
另一位觀眾則講述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自己跟老師一樣,對片子當中一段話很有共鳴,「如何去描述超越語言可以形容的事物?」,第一可能是透過詩跟愛,可能是去了解,我們所愛的人經歷過或將經歷什麼,我小時候也是看到環境很漂亮,很想要保護她,於是我就開始思考該怎麼做,其實我的人文藝術學科表現比較好,但又覺得這些專業不能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所以就咬緊牙根唸了環境工程,結果唸得很痛苦,後來我發現不對,汙染源頭其實是人,所以應該要從教育開始著手才對,就又去修了教育學程,考上正式老師,我以為自己可以在校園裡影響孩子,我在學校裡做了很多原住民文化教育,但後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處理升學。早年的我應該算是環境激進份子,我在墾丁國家公園當過志工,但我第一次面試的時候沒有錄取,因為他們說我太沉重了,遊客是來玩的,不是來聽你說教的,所以我後來就學會了練痟話(liān-siáu-uē),在解說的過程中添加樂趣,目的性不能太強。
當我們心中的愛夠大,就會知道要如何和天地萬物互動
這位觀眾繼續表示,自己有很多朋友是在NGO工作,可是他們都不快樂,因為大家的環境感知力非常的強,都想要救國救民,因此身上背負的東西很沉重,她說自己當年也不斷猶豫到底要什麼科系才能拯救地球,之後我發現拯救地球要先拯救自己,還要拯救現實。最後,我這幾年的心得是,其實不管透過什麼方式,不管是文學、影片或是藝術,這些都是工具,都是中庸的,科學也是,所以重點是我們的起心動念,當我們心中的愛是夠大的時候,它就會是正的,這時候我們就會知道如何跟天地萬物互動,落實到生活就是食衣住行方面的小地方,比如,我是我的同學中少數沒有開車的人,這意味著我出門都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有時候真的會很困難,我小時候也會為了推廣環保餐具跟同學辯論很久,然後為此衍生出推動污水下水道的想法。
這部片讓我回歸本心,加深自己對於下一代的責任
最後,這位觀眾鼓舞現場所有人,當我們心中的愛夠大的時候,當民眾覺知的力量夠多的時候,就能凝聚出一股向上的力量,在看這部片的時候,她一直在內心自我反省,這20年來到底都做了什麼,為什麼沒有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這部片讓我回歸本心,當然也很擔心,現在的孩子花在手遊上的時間比走進大自然的還要多,擔心他們會不知道要傳承什麼,而這樣的重擔就會落在我們(現場所有人)的身上,就讓我們這些還在努力的人一起手牽手加油打氣。
面對不同的生命經驗,需要透過什麼方式引導現代人瞭解現實?
聽完觀眾的回饋,洪老師也深有同感,自己在教學現場也會發現到,十年前的年輕人對於戶外活動興致勃勃,整個周末都忙得不亦樂乎,當中也產生了許多有趣的回憶和故事,現在要把年輕人帶到田野,接觸自然或現實社會,是越來越難推動,後來都讓學生們自由決定訪問自己覺得有趣或意義重大的地點或對象,結果報告交上來,全部都在訪問自己的爸媽,我只能自我安慰,他們的爸媽對他們的影響很大,透過這一件事情可以感覺到過去和現在的落差,也很羨慕片中的長輩,孩子還願意跟著家長出去野外看,這邊現場也有媽媽帶著小孩來看影片,所以我相信這樣的傳承還是很多,只是我確實擔心,我們周遭的這些東西,好像變得離現在的孩子越來越遙遠了,我覺得接觸環境變遷或許多事物不能透過ChatGPT,但這確實是現在正在發生的現實,要怎麼樣把孩子和很多不同的人丟到現實裡面,然後去了解我們的環境正在改變中,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推動環境改變或社會改革需要各種不同的角色,每個人都會有他的位置
主持人陳詩婷分享自己去宜蘭綠色影展的經驗,推動環境改變或社會改革的過程,其實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角色,比如有串聯者,有建造者,有說故事的人,有療癒者,有擾動者,有開創者,其實在不同崗位、專長,不同人格特質,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其實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們需要有人去擾動,打破既有僵化的秩序,我們也需要有療癒的人,照顧這些NGO工作者的身心靈,也需要串聯者去串聯不同領域的群眾,每個不一樣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都可以做些什麼。
台灣以前是有雪的!訴說環境變遷得靠故事
觀眾之一的黃淑德理事提出不同思考,我們看電影、聽演講或參加遊行所感受到的感動及憤怒,最後都會消退,這種情緒如何延續?台灣這幾年對冰島的興趣都是旅遊,旅遊業在COVID之後,一直在開拓新的路線,比如說去冰島看極光,台灣人的主流世界裡,還是以感官上的享樂為主,像我們這樣的群體,畢竟是小眾。前年我看了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辦的攝影展《人類世-凝視.消逝中的地表》,人類世是幾年前才提出的概念,人類對地景的改變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我對冰島的興趣是從冰島鋼琴家Víkingur Ólafsson開始的,我很想知道他們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去做這樣的音樂詮釋。我可能是在座少數還曾經去過合歡山滑雪的人,在我大學的時候還有中華民國滑雪協會,1979和1980年的寒假還有去那邊參加滑雪營,再來合歡山的雪況就不好了,只剩下滑草,要如何去說環境變遷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年輕時候的世界和現在有什麼差異,那就是要靠故事了,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台灣以前是有雪的。
人類世:面對地球,人類一點也不微小
洪老師回應,人類世的概念一開始是在講地球的地質分期,過去的地質學者會把智人出現一直到現在這段期間稱為全新世,但是在大概十幾二十年前,氣候學者克魯森(Paul Crutzen)提出,人類的活動遲早會在地層當中留下活動的痕跡,在四十六億年的時間尺度中,全新世只佔了百分之0.000065,人類世則是在短短的全新世當中,再分出一小塊,就是在說這一小段的時間裡面,人類的活動已經牽動了整個地球的系統,已經可以在地球的地質紀錄裡面留下痕跡。
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超越火山爆發、超越冰河期
人類活動的加總,已經可以超越任何一次大規模火山爆發帶來的影響,它可能比任何一次冰河期的影響都還要大,我們的活動已經可以牽動整個大的地球系統,那個人類世的起點可能是18世紀工業革命,人類開始大量挖取煤炭燃燒,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也有人會訂在15、16世紀哥倫布大交換,開始去入墾新大陸,造成大規模當地原住民的死亡,大規模的從非洲將人類運到莊園,雖然人類世開端的定義眾說紛紜,但我們這些社會學家會有個共識,我們現在已經活在一個,面對地球面對自然,人類不是什麼微小受自然支配的時代,人類對地球的影響規模,不管是空間範圍還是時間尺度,都遠超過任何一個人和任何一個社會所能想像的,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淡水河受到汙染,或是家門前的小河被偷排廢水,我們在談的是一個巨大到超越我們身體能感知的尺度。
我們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認識越多,對周邊環境的改變就越少
洪老師跟觀眾分享,最近看了安清(Anna Tsing)寫的《末日松茸》,作者提出一個主張,人類世牽動到的尺度越大,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越在地的觀察紀錄周邊發生的事情,因為她注意到一個很大的落差,我們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認識越多,對周邊環境的改變就越少,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是牢牢記得、描述,去講周遭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去保留這些有趣的微小的細節。
冰島的冰川消融和帛琉的海平面上升,是同一種遺憾
一位帶著孩子一起觀影的媽媽表示,我和兩個孩子這兩天看了小公視上,一個有關氣候變遷的節目,節目小組有去斯瓦爾巴群島參訪全球種子庫,也有去到帛琉看高腳屋(為了應對海平面上升),我發現到這樣的節目內容其實是能觸動到孩子的,剛剛影片裡有講到,冰島上的冰是以一年一公分的速度在融化,而現在同時有一百多座冰山同時在融化,一年就是一百公分,因此這個海平面的抬升是很巨大的,讓我感覺到相當震撼。

核電站-300x253.jpg)
-5-1-3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