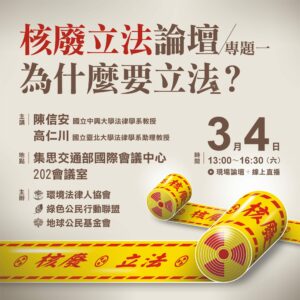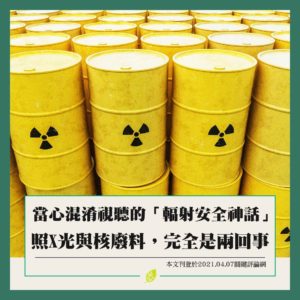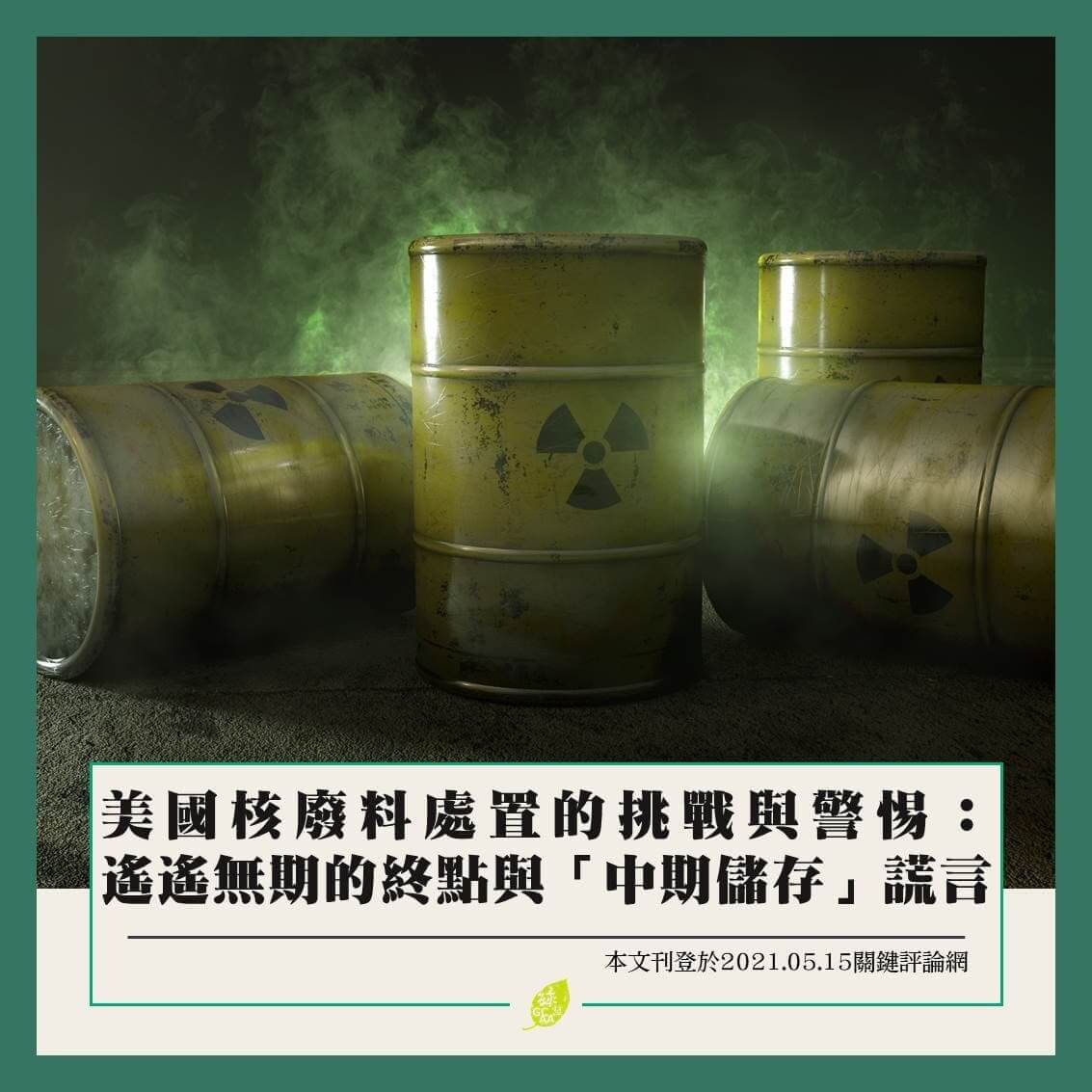
台灣民眾常誤以為,在最終處置設施完工、啟用前,高階核廢會暫存於中期儲存設施,此外,高階核廢的中期儲存和最終處置是兩個不同的議題。實際上,核廢「中期處置」很可能會淪為「露天最終處置」。
今年年初由美國反核團體和州政府就核能管理委員會違法核發中期儲存設施的建照,所提的訴訟就顯示,中期儲存設施的增加和最終處置設施的闕如並非是兩個議題,而是同一個結構問題的兩個面向,因為聯邦政府根本無意妥善處置高階核廢,只想藉由興建中期儲存設施之名「快速解決」核廢。
案件要先從美國知名反核團體超越核能(Beyond Nuclear)說起。該組織指陳,依據美國國會於1982年所訂的《核廢料政策法》(The Nuclear Waste Policy Act),美國民生用途高階核廢應存放於最終處置設施。在該設施啟用前,能源部不得接收核工業所轉移的高階核廢。但核管會卻藉由核發中期儲存設施「暫存核廢120年」為名,使得核工業者可於最終處置設施闕如的情況下自核電廠移出核廢,並使能源部得以變相接收核工業者自1950末期以來所累積的高階核廢。
為此,超越核能已於2021年2月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要求核管會撤銷(違法核發給核工業者在德州與新墨西哥州邊界興建)中期儲存設施的建照。
在超越核能上訴後,新墨西哥州司法部長巴爾德拉斯(Hector Balderas)也於2021年3月29日對核管會允許業者在該州及德州興建高階核廢料中期儲存設施提出訴訟。
新墨西哥州政府指稱,核管會先藉由中期儲存核廢為名,讓業者違法轉移核廢給聯邦政府,之後再以中期儲存取代最終處置。此舉形同迫使當地部落與社區世世代代承受高階核廢永留該州,並迫使居民曝露於輻射外洩的風險。
要探究核管會違法核發中期儲存建照的爭議,就得先回到事情的源頭,也就是美國最終處置所牽涉爭議。我們才能理解中期儲存、最終處置為核廢的一體兩面,且聯邦政府自二戰以來,在核廢問題上一事無成。
官方數據顯示,至2020年為止美國總計有83,000公噸用過的燃料棒,用過的燃料棒目前以每年2,000公噸的速度持續增加。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美國現有核電廠除役所產生的核廢。聯邦政府宣稱,美國第一座最終處置設施擬於2048年完工啟用。但官方始終說不清楚,該設施的地點是否仍在內華達州猶卡山(Yucca Mountain)。
換言之,即使該設施真能啟用,美國屆時仍有約69,000公噸的高階核廢無處可去。而2048年距美國在二戰後有計畫地發展兩用反應爐(也就是既能產生核武所需要的鈽、鈾,又能用於發電的反應爐),卻始終無法安全處置高階核廢,已長達一個世紀。
有人好奇,美國地廣人稀,領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及加拿大,為何最終處置設施卻遲遲未完工?美國國會於1982所訂的《核廢料政策法》賦予能源部主導最終處置設施的選址和建造規範。但美國聯邦政府一再輕率對待最終處置議題,拒絕面對處置高階核廢所涉及的政治經濟、科學、公衛、環境、氣候等問題,使得核廢困境治絲益棼。
在《核廢料政策法》生效實施後,能源部於1984年12月公布了3個最終處置候選場址,地點分別為內華達州猶卡山、德州聾子史密斯郡(Deaf Smith County)、華盛頓州漢福德核武廠,而漢福德場址也是全美輻射污染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能源部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各界撻伐。公布場址後的6個月內,3個州政府已分別對能源部提告。
州政府所提的訟訴並非無的放矢。美國國家審計局(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於1985年的報告指出,能源部的環評欠缺科學依據。同年美國環境保護局也認為,能源部所用數據的研究目的與最終處置並無關係,數據根本無法佐證該部的選址理由。
不過,州政府所提的訴訟和質疑卻使得聯邦政府在候選場址的立場更為專斷。為了「有效消弭」訟訴爭議,國會和能源部遂於1987年修正《核廢料政策法》有關候選場址的條文,以使能源部毋須找尋多個候選場址,只要直接決定一個場址即可。如此一來,不但立即消弭了「『候選』 場址」的爭議,也促成了內華達州猶卡山成為全美唯一的最終處置場址。
問題在於,自聯邦政府「依法行政」專擅最終處置場址和規範最終處置設施以來,從未正面回應各界所提的六項主要質疑。
首先,內華達州並不使用核電,為何卻得承受能源部強加核廢危害於該州的危險?第二、聯邦政府自1951年以來於該州試爆核子武器高達928次,其中828次為地下核武試爆,使得該州人民長期曝露於輻射危害。但政府卻始終以「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為名,迴避民眾的質疑與批評。
其三、能源部球員兼裁判,一手包辦生產、丟棄高階核廢、規劃、監督最終處置為時已久。能源部不僅統合能源生產,也替美國海軍生產核子反應爐,並設計、測試和生產美國所有的核子武器。
為處置製造核武所生的核廢,能源部在新墨西哥州奇華環沙漠(Chihuahuan Desert)設立了「『廢料』隔離試驗設施」(The 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
美國政府自詡技術領先全球,一遇廢核,卻紕漏不斷。該「『廢料』隔離設施」於2009年時發生有毒的四氯化碳外洩超過半年。該設施再於2014年發生地下大型運輸車起火、爆炸意外和21名工人因曝露於鈽239、鈽240和鋂241因此罹癌的事故。而納稅人為能源部的輻射事故付出了至少20億美金的費用。能源部所說的「『廢料』隔離設施」倒也名符其實。官方等同核廢為「廢料」,所以該「廢料設施」根本無法隔離輻射。而能源部在事故發生時,卻一再以「國家安全」之名封鎖消息,迴避外界監督,使民眾更加疑慮最終處置的安全性。
第四、內華達州地震活動頻仍,高居全美第4位。美國國家地質調查局指出,自1976年至2010最終處置場址半徑80公里內已發生621次芮氏規模2.5以上的地震。地質調查局並於2007年坦承,斷層帶經過最終處置設施的影響遠高於先前的估計。
但最終處置所面臨的地震危害並非只是百萬年而已。以百萬年的尺度評估最終處置,不僅低估了高階核廢的輻射危害,更是高估了美國處置核廢的能力。以運轉核子反應爐所產生的碘129為例,半衰期長達1,570萬年。美國不僅得面臨科學不確定性,又因欠缺實際除役和中期儲存經驗,以致無法正確估計核廢最終處置的成本。
當能源部在新墨西哥州尚且無法妥善「隔離」核廢料,外界又怎能相信,能源部在地震頻仍的內華達州,反倒更有能力規範、監督最終處置設施,防制輻射的危害?
第五,美國《核廢料政策法》賦予能源部主導最終處置設施的選址和建造規範,而該法卻刻意弱化地質、水文、環境的科學評估機制。該法雖明定,地質條件是選址的最重要因素,卻無相關條文確保能源部的政策必須以科學評估為依歸。例如該法第112節明定,能源部選址時應利用「既有」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地質、水文數據即可。該法第404節更載明,能源部為選址而鑽探時,直徑不得超過40英吋,也就是101.6公分。
簡言之,當使用既有數據的目的與設置最終處置設施兩者並無直接關係,《核廢料政策法》要求使用既有數據,無非是在迴避探勘地質和調查水文。既無地質、水文研究,自然不會出現地層滲水、最終處置設施結構堪慮的結論。而能源部一意規避現今科學知識,力求從速、從寬、從權設立最終處置設施,落得事與願違當然不令人意外。
最後,猶卡山為印地安人傳統領域,當地居民社經地位較差,所以能源部自1980年代開始尋找最終處置場址與中期替代方案時,便一力排除全國地質調查,直接鎖定原住民部落,吃定居民較無能力反抗。有鑑於聯邦政府持續在內華達州試爆核武,再加上選址從不徵詢居民意見,幾十年來已使得該州民眾反核武與核廢的意識高漲。
自《核廢料政策法》生效實施以來,能源部已自1983年至1987年間,陸續與核工業簽訂制式合約,表明最終處置設施最遲會於1998年1月31日開始運作,能源部屆時會接手處置高階核廢。
因前文所說的諸多爭議數十年懸而未決,美國聯邦政府不得不一再延後最終處置設施的啟用年度至2048年。
因能源部無法依據《核廢料政策法》(The Nuclear Waste Policy Act)規劃和完成最終處置設施,得使高階核廢無處可去,核工業遂對能源部提出賠償訴訟。核工業自行估算的賠償金額截至2020年已高達500億美金。而能源部的估計,在計入最終處置的營運和維護,費用則高達7兆美金。不論實際金額究竟為何,能源部所支出的一切費用還是得由美國納稅人承擔。
為了替能源部所面臨的賠償滅火,也替核工業的高階核廢找個省錢的去處,核管會遂允許核工業於德州和新墨西哥州興建高階核廢中期儲存設施。
然而高階核廢以「中期儲存」之名永遠留在當地不僅會危害水資源、農業、環境及居民,露天中期儲存設施一旦遭遇恐怖襲擊、飛機失事和自然災害時,更是不堪一擊。核管會意圖大舉移置全國高階核廢至德州和新墨西哥州,不僅無法達成核廢應與生物圈安全隔離的最基本要求,反倒大幅增加輻射災害的風險。
讀者會提問,核管會核發中期儲存設施的興建執照,為何無法替最終處置設施的闕如暫時解套?
依《核廢料政策法》的條文,能源部得以兩個替代方案暫存高階核廢,興建聯邦監測「可恢復儲存設施」(monitored retrievable storage)或興建中期儲存設施。兩個替代方案的實質差別只在於「中期」儲存期間究竟為50年或百年。
這裡先從第一個替代方案說起。要於全美任何一州或印地安部落找到同意於該地興建聯邦監測可恢復儲存設施時,聯邦政府過往是否嚴謹地防制輻射危害就成了取信於民的關鍵。
早在1985年能源部就選了田納西州的橡樹嶺興建聯邦監測可恢復儲存設施。但能源部從未說明該設施的效益為何,使得計畫遭到居民強烈反對。
一般而言,跨越全美運送核廢料與大量集中核廢料於監測設施本身就具有高度風險。而運輸風險包括先運輸全國核廢至該州,再於最終處置設施啟用後,運送核廢至最終處置設施。
問題在於,當乾式儲存可以做到隔離,能源部應就兩次全國運輸和集中高階核廢於一處提出輻射防護計畫,並說明集中儲存的必要性和效益。美國政府問責局直言,能源部根本無法說明替代方案是否必要和具有任何效益。
至於第二個方案興建中期儲存設施也有跨越全美運送核廢的疑慮,這也是超越核能和新墨西哥州政府所提的質疑之一。此外,核管會違反《核廢料政策法》核發中期儲存設施的興建執照,形同接受核工業轉嫁廠內儲存核廢的成本給美國民眾。
超越核能和新墨西哥州政府判斷,中期儲存會淪為「最終處置」並非杞人憂天。
早在1979年時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已於判決書要求,在美國尚未設立最終處置設施前,核工業應於廠內儲存核廢、責無旁貸。
核管會曾於1984年要求,核工業必須在核電廠關閉後在廠內安全貯存核廢料30年。能源部當年認為,最終處置設施最遲會於1998年1月31日啟用。核管會則認為,該設施會於2007年至2009年間起始運作。
猶卡山爭議湧現後,核管會已於1990年代推遲最終處置起始運作的時程至2025年。但在猶卡山爭議歷經30年依舊未決,核管會只得於2010要求,核電廠關閉後,核工業必須在廠內儲存核廢60年。
因核管會所定的60年期限完全欠缺科學和環境影響評估的依據,紐約州政府和環保團體遂對核管會提告。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2012年6月8月的判決書中明言,核管會並未考量美國永遠不會出現最終處置設施的可能性及影響。此外,核管會並未依據科學具體評估核電廠關閉後,廠內儲存核廢60年可能的危害。
核管會在敗訴後於2013年坦承,因最終處置遙遙無期,依據綜合環境影響報告(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的結論,並不排除核工業可能必須在廠內無限期存放核廢。
為了替核工業解決1570萬年都不得除役,核廢料求出無期的困境,核管會遂違法核發中期儲存設施建照。如此一來,核工業可以堂而皇之地移轉核廢給能源部,而能源部再轉嫁費用給納稅人,並強加核廢永留當地的後果給居民。這也是超越核能和新墨西哥州政府為何要對核管會提告的原因。
美國的訴訟值得台灣社會關注的原因在於,超越核能和新墨西哥州政府所提的訴訟並非只是普通的環境訴訟,被告並不是製造污染的跨國企業,而是核管會,也就是軍工複合體的組合部分。核管會之所以違法全是為了替能源部和核工業分別解套。能源部正是軍工複合體的核心。
從美國核廢的最終處置、中期儲存可以清楚看出,美國聯邦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門一遇到核廢,就先射箭再畫靶,只求眼不見核廢為淨,獨斷專行,置科學依據於腦後。
但是美國軍工複合體(也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門)輕視與除役、核廢相關的科學、技術、知識生產並非特例,這正是各個核武/核電國家的常態。台灣亦不例外。原能會、台電事事以美國核管會/核工業漠視科學的立場為依歸,就可見一斑,言必稱「核管會認為可以」、「核管會沒說不可以」。這類拿著雞毛當令箭的行徑,不禁使人質疑,美國核廢求出無期的困局和教訓,台灣的主管機關和公用事業體究竟是真的忘記,還是害怕想起?
再回頭看看國內歷任政府如何漠視輻射安全、從權達變。台灣連核四都能搞成最昂貴的爛尾工程,「封存前多項設備尚未通過測試,一號機大量挪用二號機零件,遭監察院糾正;部分零件目前已停產,備品取得困難。不按圖施工、違法變更設計、設備多次泡水、起火等」。至於現今政府高官更為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稀釋後可以喝」背書,不禁令人懷疑,台灣日後是否會走向美式「中期儲存」的滑坡?
雖然目前無法確知續建核四和日本核廢水爭議會如何發展,但從超越核能和新墨西哥州政府所提的訴訟倒是可以明確看出,我們難以指望資產階級能嚴肅看待除役和高階核廢所衍生的複雜問題。若台灣產官學既得利益團體執意以美國核管會的立場馬首是瞻、亦步亦趨,台灣的除役與核廢難題也會註定無休無盡。
本文刊載於2021.05.15 關鍵評論網
★綠盟5/18晚上7點舉辦跨國連線演講:如何抵抗核工業的環境不正義?從美國環境運動談起,邀請超越核能的核廢監督專家Kevin Kamps以線上方式與我們進行座談,歡迎大家到綠盟粉絲專頁收看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