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到氣候時,很少人會思考殖民時期所遺留的土地問題與氣候變遷,兩者究竟有何關連?
希臘導演馬齊亞拉基(Daphne Matziaraki)和肯亞導演穆里米(Peter Murimi)在《肯亞荒旱之戰》以肯亞白人家庭,以及半遊牧民族桑布魯人的衝突,探問前述議題。雙方原本相安無事,卻由於氣候變遷,乾旱肆虐,現今勢同水火,進而帶出非洲政治經濟體制之於氣候災難的影響。
桑布魯人在當地放牧牛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他們除了牛羊,身無長物。當地與「生命」有關的詞語,係由「牛」字所衍生。牛群不僅提供牛奶、血液、肉食,也是半遊牧民族生命的重心。牧民隨著季節遷徙,更換牧地,在平時是傳統,在旱季,艱辛求生,當大旱成為常態時,則事關存亡。
牧場主人則大多為英國殖民者後代。片中家庭自先祖殖民肯亞,定居至今,已有四代,他們在肯亞的歸屬感源於擁有一望無際的土地,富饒水草,所帶來的優沃生活,而土地則為白人繼承而得。
殖民者後代認為,擁槍自重,以圍籬圈地,維護私有財產權,天經地義。即使乾旱經年累月,危及桑布魯人與牛羊的生存,以武力排除當地牧民進入土地,也是理所當然。
記錄片並未著墨於殖民史。影片卻顯示,當地牧場主人對於殖民統治所建立「井然有序」的時代,頗為懷念。他們並不關心,也避而不談先人究竟是以什麼手段取得土地。
英國於1895年7月1日宣告肯亞為英國保護國。英國1920年方才宣布肯亞為殖民地。英國在「保護」、殖民肯亞期間,以軍事鎮壓與當地民族「溝通」土地「所有權」。
英國覬覦肯亞已久。當地平均海拔1,500公尺;東部低,西部高。由於農業土壤肥沃,氣候宜人,英屬南非公司旗下的東非辛迪卡(East Africa Syndicate)遂於1902年4月率先提出取得1,300平方公里肯亞土地。類似案例其後接二連三而來。
不列顛東非公司殖民長官霍爾(Francis Hall)曾道,要「改善」當地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消滅他們。我很樂意動手,不過我們得依賴他們供應糧食」。該公司係為英國在肯亞、烏干達兩國的殖民政府前身。
英國持續掠奪土地,再分配給定居殖民者,也成了英國資本積累的手段之一。由於失去賴以維生土地,使得肯亞當地民族,淪為白人農場或城市的賤價勞動力。
即使如此,桑布魯人仍然堅持自身的傳統。
美國歷史學者埃爾金斯(Caroline Elkins)以英國官方檔案、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於其專著《英國的古拉格:帝國在肯亞的殘酷終結》(Britain’s Gulag: The Brutal End of Empire in Kenya)詳細分析,英國為對付肯亞反殖民運動所建立的集中營,並以大規模刑囚、虐殺基庫尤人(The Kikuyu),摧毀抵抗。
當時反殖運動的主要訴求,就是要求殖民政府歸還強奪而來的土地。英國在撤離肯亞前,已大量銷毀官方記錄。英國在當地的軍事鎮壓的規模、刑囚和凌暴,其殘虐程度為大英帝國鎮壓反殖運動之最。
查爾斯國王於2023年出訪肯亞時,面臨該國各界要求英國就肯亞爭取獨立期間的種種罪行道歉。他僅僅表示,英國在過去曾有「不合理的暴力行為」,卻拒絕道歉,並就過去的 「錯誤行為」,表示 「遺憾」(regret)。
英國表達「遺憾」卻拒絕道歉,係指「遺憾」肯亞人「念念不忘」陳年往事。若我們從壓迫者國家的立場,對照影片白人牧場主人自身所呈現的敍事,就更能體會牧場地主的「懷舊」之情,究竟從何而來。
本片並非一面倒,只呈現桑布魯人的觀點,而是如實展現出牧場家庭遭桑布魯人侵門踏戶時的恐懼。而半遊牧民族的暴力行為,原因並不在於搶劫財物,而是在於報復牧場主人,在大旱之中,蓄意殺光牧民牛羊,斷人生路。
《肯亞荒旱之戰》彰顯,肯亞取得政治獨立已超過60年,但該國資產階級始終無意面對,更遑論解決國內盤根錯節的土地和不平等問題。
現今統治者所捍衛的利益,與殖民時期的利益,雖然形式有別,本質卻相同,懸而未決的問題,再為肯亞底層民眾的生存,火上加油。
本片情境也是非洲各國底層民眾境遇的縮影,值得觀影者以同理心,一起走入絕境求生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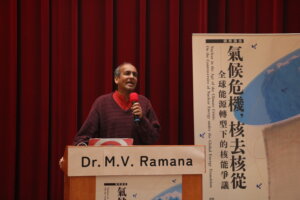

-12-3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