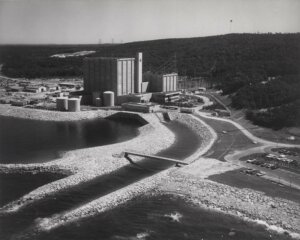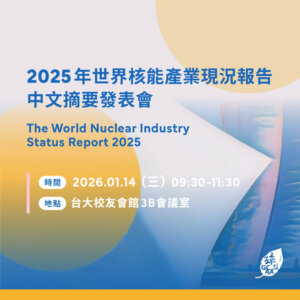「看到差異的能力比統合還重要」綠盟在20週年系列講座「不只是環運:社運議題的交織與協力」中,由來自人權運動、性別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等跨領域的資深社會運動工作者一同座談,走過尋求議題的相關連之處,再走向看到理念相近的團體之間的彼此差異,重新看待今日台灣與社會運動的意義,這些老戰友們認為,先看到彼此不同,再談是否同意,也許是現今討論公共政策的新課題。
「一方有難、八方來援」關注不同議題的社運團體長期互相聲援,放大相通理念的聲量,撐出台灣民間的生猛活力。「與其說支援,不如說議題本來就需要很多人的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回顧,在解嚴前就已經成立的台權會過去歷史,早期便參與了原民、婦女權益、搶救雛妓、廢除刑法一百條、阻止人口販賣等議題,更在2000年跟性別團體合辦「人權婚禮先修班」,提醒當時的政府婚姻除了遵守一夫一妻外,還有更多思維需要再進步。近年為了聲援婚姻平權,台權會更將會旗與Logo調整為六色彩虹,宣告其挺同立場。
如今在倡議上,不同團體仍需要分工,一起打組織戰,並非只是聲援而已,施逸翔舉例他們目前關注的外籍漁工權益,跨了人權、勞權,而數位身份證的討論上,至少在性別、姓名的欄位上,就有關性別團體、原住民團體等。
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曾嘗試連結勞工跟性別,在爭取婚姻平權上,也促成人權與性別團體合作,互相結盟協助。回顧周于萱自身的經歷,即是從聲援勞權、土地開始參與起公共議題,一度在「聲援別人之外怎麼定義我自己」迷惘,但在負責「鐵馬影展」的幾年中得到養分,透過影片瞭解了國內外社運的異同,更體會了議題並非第一線在街頭推擠抗爭,還有很多的途徑與角色。「這並不是曇花一現的活動」周于萱認為,這是一個與社會溝通的機會,否則也許有些民眾一輩子都沒有機會開始審思自己的勞動處境。

近年包括反核、同志大遊行、氣候變遷的街頭行動,都可看到外籍移工參與的身影,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盡力捲動他們參與。TIWA研究員吳靜如表示,各方開始在議題上互相理解對方的需求,是讓他感動的部分。
回首2013年印尼看護工不慎摔死知名作家劉俠、另一外籍看護工在過勞下發生精神失常殺人後企圖自殺等事件下,看護工的勞動條件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看護工幾乎每日24小時的照顧,更與照顧者產生了超緊密的關係等等面貌逐漸獲得關注與討論。吳靜如表示,當開始要談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時,當然有長照需求的家庭、身心障礙團體曾經擔憂影響自身的權益,但經過社運團體的協助下,身心障礙團體與移工漸漸理解彼此,更能上街頭相挺為對方發聲,讓他非常感動。
而環運與工運「紅綠」兩者長年分分合合,近年在違章工廠失火事件再現合作,環境破壞與勞權侵害,甚至消防員的生命安全互相綁在一起,各方一起看向資訊公開的重要。一掃過去當環團要求工廠改善時,員工反而擔憂對自己工作不利而噤聲的狀況,過去即便環團試圖提醒在污染場址工作,工人面臨健康威脅,但往往很難開啟對話。
倡議團體希望並非在悲劇發生時才被迫合作,持續設法串連整合,因此,如何讓自己的支持者理解聲援其他領域的理由,也成為挑戰,其中又以廢死議題最不討喜。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回憶,過去曾經在廢死聯盟表態支持婚姻平權時,遭部分同志朋友抗拒反彈,但他反問,為何會有誰不可以支持同運這樣的想法?如此豈非正是歧視?
而2014年因318反服貿、4月反核遊行街頭沸騰時,政府再一次選擇以執行死刑來轉移民意焦點,林欣怡表示,當時非常自責廢死議題拖累了社運伙伴,然綠盟秘書長崔愫欣則是抱著「我們的運動導致有人犧牲」的沉痛心情,因為他們的抗爭行動讓一個還在搶救中的死刑犯被提前處死,因此第一次與廢死聯盟一起前往司法院抗議,也親身承受了一些民眾特地跑到記者會場謾罵嘲諷,體會了廢死議題所受的壓力。

面對目前網路間訊息流傳快速,民間對於社會的關注與焦慮感,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討論風氣,目前「網路辯論多,但上街的人變少」的狀況倡議團體也正在學習如何自處。
周于萱回憶,當總統蔡英文當選第二任,理當落實性別政策承諾時,卻發生閣員性別比例更懸殊的現象,婦女新知發表提醒,卻面臨了持續約一週的抨擊,「中國同路人」「扯後腿」「總統都是女性了你們這些女權主義者到底還要什麼」「台灣已經夠平等了吧」…甚至連他們自己原本的支持者也有些「為何要在這個時候提的」質疑聲。
而目前一旦發生任何性平事件,「婦女新知怎麼沒出來講話?」的質疑也總是隨即出現,周于萱表示,他們認為事情需要得到公正調查,並不能看到新聞、聽到一句話就輕易下定論評判。
「但這就表示踩到痛點了。」施逸翔表示,台權會倡議的話題往往並不太受關注,因此發生被「出征」時也表示「有人在乎」,表示這次的發聲是有激起討論效果的,議題可以曝光,倡議團體倒是不用太心急處理不同意見的網路留言,因為他發現會有支持者自動幫忙回應,而形成討論。
「我們不處理留言了,我們把時間跟力氣拿來辦活動當面溝通。」林欣怡表示,廢死聯盟在網路上有時會收到「給你好看」之類的兇狠留言,但有些太荒謬的,大家自有公評。但若有機會當面溝通,這些充滿正義感但卻也因所得資訊有限而腦補了很多想法的「鍵盤法官」,卻反而有可能重新想想。吳靜如也直言TIWA對他們的臉書,也已經「沒有力氣回應了」,但不同意見者若願意打電話、當面來討論,就有空間溝通,可惜目前移工仲介組織完全不願意跟他們辯論。

過去民眾有意願以身體當武器,上街頭去衝撞體制的草莽氛圍已變。但面對更為細緻的討論,倡議團體也開始認知,從相挺、整合的團結,先面對彼此的差異,也許是現今公民討論的基礎。
過去倡議團體以「聯盟」「平台」互相團結,各自出力於共同的目標上,但被視為同一個團體後,個別的差異也就可能在運動策略上先被犧牲了,例如性別團體合力爭取婚姻平權時,為了避免模糊焦點,只能先以最大公約數去推動議題,婚姻以外的單身者權益等就暫時無法著力太多。
正如目前的代議政治型式,在選擇一個民代時,選民沒辦法得到一個理念完全相同的候選人,只能挑選契合的程度最高者,但當選後卻所有的理念都被他給代表了一般,各自不同的倡議團體,也不願被泛稱為一體視作理念都相同的,對他們而言,先看到各自的不同,再從中討論出共識,應是未來團體間、公民間討論議題的能力。「看見差異比統合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