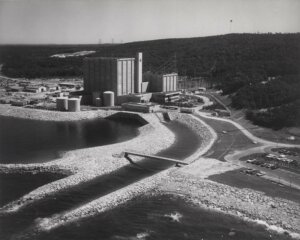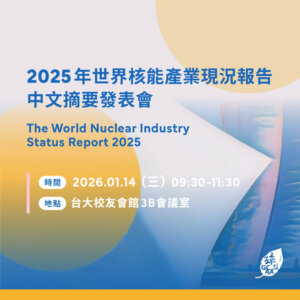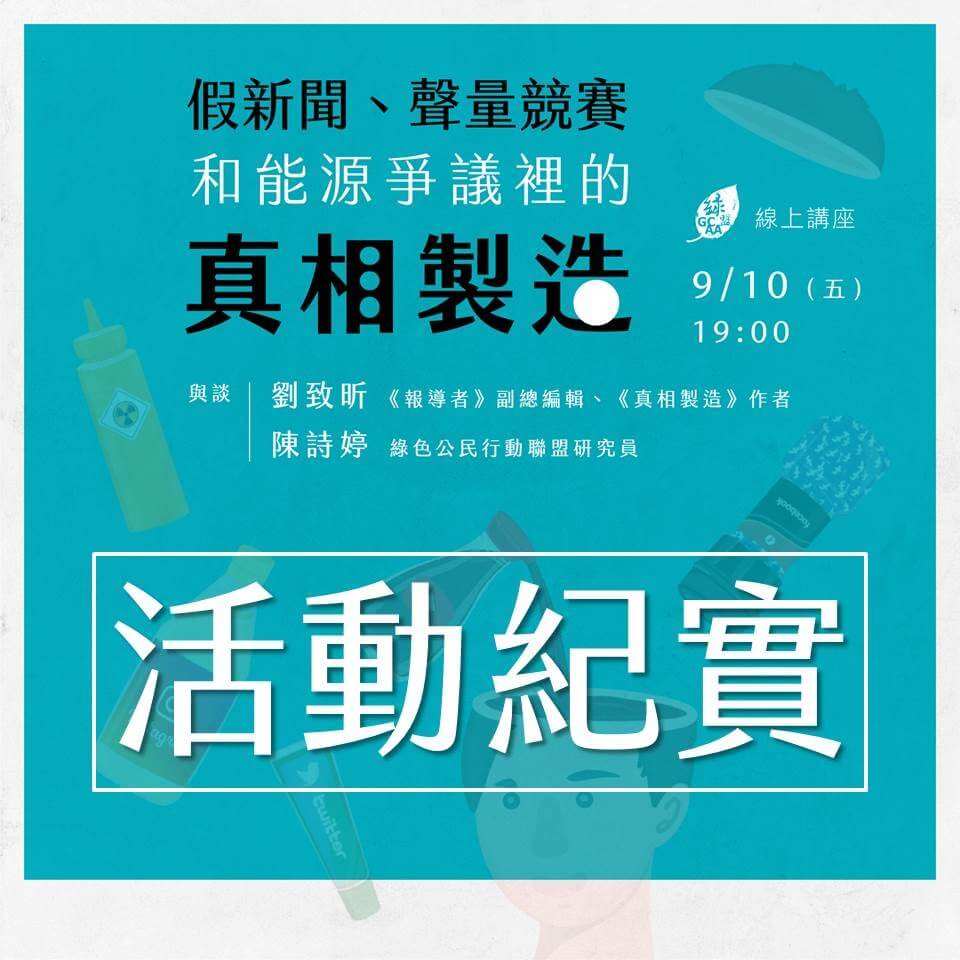
在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裡,真真假假已難以分辨。藉由操弄網路輿論,可以使穆斯林青年成為恐攻分子、可以跨海介入另個國家的總統大選,使社會分裂。網路訊息傳播的快速便利,對人民來說究竟是糖果還是毒藥?
我們邀請到《真相製造》作者劉致昕與我們分享,書寫此書試圖重新釐清每個人與真實的距離,也令我們反思真相製造產業鏈背後的社會樣貌,往往比社群媒體中呈現的二元對立、黑白善惡來得更加複雜多變。
以下就來看看這場講座紀實吧!
在川普贏得美國大選之後,有一位現在被稱為「假消息教父」的人浮現檯面,他聲稱自己是「不小心幫川普選上總統的人」,引起全球嘩然。雖然抹黑、造謠是選舉中常見的競爭手段,但這一次不一樣,真假難辨的消息在網路上快速流竄,比起過去電視辯論或新聞報導的途徑更令人措手不及。他甚至不在美國,而是位在遙遠的馬其頓。
記者試圖進一步了解他的動機,他原來是一名網紅,有天收到一則邀請:只要傳播似是而非的消息,稍微竄改一點內容、編故事,憑藉他的流量將假消息傳播出去,每月便能獲得數千美元的收入;經濟利益和隨之而來的成就感支持他持續做下去。
講座的開始,劉致昕分享大西洋委員會資深研究員Ben Nimmo 的一段話:「數位出版科技的普及讓建立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社群媒體讓發布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社群媒體讓散布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不實內容包括爭議性、挑逗性、挑釁的、敏感的、偏見的、偏頗的、抹黑的資訊等。過去建立、發布、散布資訊的權力僅限於媒體,但數位時代的來臨讓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媒體,成為資訊的製造、發布、散布者,並且不需要經過證實,也不受監督;甚至演算法會讓那些較情緒化、煽動性的言論更容易被看見。2018年美國期中選舉前,臉書創辦人祖克伯發布一篇文章中指出:越靠近社群規範紅線的內容,流量和互動性越高,雖然使用者們總是說他們討厭這樣的內容。
為了瞭解這些散布不實言論的人背後的目的,劉致昕花了五年時間、橫跨八個國家進行採訪。他發現不只有賺錢的人,還有生氣的人、開心的人、受傷的人,他舉了幾個例子說明。
法國許多年輕人對高失業率、選舉結果不滿,對體制、媒體、政治都感到不信任,他們漸漸在匿名論壇上形成次文化。法國極右派政黨在匿名論壇支持、發布極端言論,諸如仇女、排外、脫歐等。極右派政黨利用這些極端言論網紅化,吸引年輕人,便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得了選票。這些年輕人似乎獲得了認同,便從生氣的人轉變為開心的人。
2019年印尼大選在兩大黨以外,橫空出現第三位候選人Nurhadi,他的政見包括「地層避震器」以及「海嘯消滅器」,他呼籲民眾如果不支持就不要投票;荒誕的言論卻吸引了80多萬人支持。這名候選人的照片取自一位50歲的按摩師,但幕後使者卻是21歲的年輕人和幾位年齡相仿的朋友。他們的家鄉、農田、家人都飽受自然災害威脅,曾經支持的候選人卻不作為。他們決定製造一個虛構的角色對抗貪腐、無能的政府,政見反映出人民真正在乎的事。這個假,卻是出於真。他們不是賺錢的人,也不是開心的人,他們是受傷的人。
透過這些故事,劉致昕鼓勵我們去想像、思考生活中有哪些生氣的人、開心的人、受傷的人,避免一味批判假訊息,試著瞭解背後的故事。
綠盟研究員陳詩婷認為現在是「後真相時代」,這不意味著真相不存在,而是「事實沒有我的觀點來得重要」。人們依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來理解事件的比例提高,依據事實來詮釋的比例下降。人們開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專家,甚至可能用扣帽子的方式來理解對方,找到事實的共識變得非常困難。
陳詩婷歸納出能源轉型倡議的困難有以下6個原因:1. 氣候危機非常緊急,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大尺度的系統性轉變,人們難以在短時間改變習慣。 2. 數據可能是對的,但卻被放在錯誤的或片面的脈絡中,造成有偏誤的詮釋。 3. 人們容易把相信「科學家」錯當成相信「科學理性」,極端地將不相信那名科學家意見的人視為反科學、理盲、側翼甚至是政府打手。 4.文組和理組的衝突,崇尚理科、技術,排斥多元意見的討論容易忽略社會影響。 5.二元對立、弱弱相殘,譬如當一方談論核廢料貯存場鄰近居民的犧牲時,另一方以空汙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回擊,但這樣的討論並無助於解決問題。 6.「都是他們的錯!」強硬地將責任推給執政黨或在野黨或某個團體,彷彿只要他們消失就能解決問題。
這些困難都讓冷靜、理性的對談難以進行。而能源轉型除了使用更永續、更乾淨的電以外,也希望以更公正、民主的方式發電,用更智慧、高效的方式用電。要將原來大型、集中的發電方式轉型成小型、分散的智慧電網,做出分散風險的韌性系統。這些轉型需要和許多公民溝通,讓民眾不只是能源的消費者,而是同時兼具生產者的身分。除了和民眾溝通以外,也需要和電廠對話,將汙染和風險等外部成本內部化,讓過去封閉的經營模式改變成開放的治理模式。
但這個不利於能源議題溝通的狀況是如何形成呢?如同劉致昕提到法國的案例,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缺乏民主參與,人民漸漸不信任政府、媒體、專家。有意的民粹只要操作打擊政府的人設或極端言論就可以吸引不信任政府的人,根本不需要考量資訊來源是否經過查證,只需要考量是不是符合他的利益, 能否吸引到流量和聲量。鬼扯的言論因此在數位平台肆虐。大數據讓閱聽者重複看到和自己意見相同的聲音,就會以為這些破碎的事實或捏造的資訊就是真相。
作為倡議者該如何在假消息的夾縫中生存呢?陳詩婷建議避免扁平、簡化的答案,在溝通的過程中將容易被誤導或難以理解的資訊變得白話,但不去簡化它,以免變成片面的資訊或脈絡。也要建立不同專業領域之間的互動整合,或是專業與非專業之間的協作,重新練習民主。我們可能會預設不認同氣候變遷的人肯定也反對潔淨能源,但事實上卻可能從私有財產、創新、國家安全等角度找到共識或結盟的可能性。
講座的最後,劉致昕鼓勵大家用好奇心去理解跟你不一樣的人們。這個時代大家都太忙碌了,或覺得反正隨時都連絡得到,所以就用很多快速的訊息或是很簡單的語音來保持認定的溝通。可是這會產生很多人際關係上的斷裂,衍生出上述種種社會問題。在某些情況下,比說服對方或是叫對方改變,想辦法創造一個聆聽彼此的機會其實也是一分功夫。
陳詩婷則提醒:當你有一個價值的時候,勢必會有跟你站在不同位置的人,但其實這個時代,很多制度跟文化,很多人的聲音其實是沒有辦法被聽見或認同的。或許不是去消滅或對抗,或是很快地去區分同溫層或異溫層;相反地,可以去思考怎樣把民主溝通的文化建構得更健康。
「媒體識讀」聽起來是無聊的陳腔濫調,但執行的細節卻有許多新的方法。多元涉略、探詢動機、避免過早分類、傾聽與溝通等等,這些都能幫助我們朝真相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