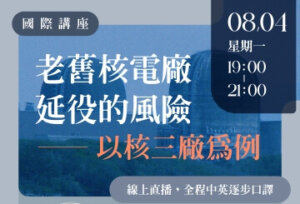「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故事,能夠打破封閉不語的自我牢籠,揭示一個更寬更廣的現實,並充分展現其中的相互關聯?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避開常見的、顯而易見的、沒創意的陳腔濫調,轉而以非中心的、遠離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Olga Tokarczuk的得獎致詞,道出當前存在於各領域的暗影:在碎片化、虛實難辨的訊息中快速選邊站,甚至快速仇恨或喜愛。紀錄片「里奇蘭小鎮」裡,美國學者與導演Irene Lutzig示範了一種與暗影共存的可能方式。她帶著一本里奇蘭地方詩人的詩集,花費數年一再走訪這個位於美國西岸華盛頓州東南部、因戰爭與製造原子彈而發展的城鎮,探索鄰近製造武器級鈽的漢福德工廠在居民身上留下的軌跡——如何究責上一代的痛苦,以及如何持續、有機地旁觀他人的痛苦。
這裡的高中足球隊與管樂隊暱稱為「轟炸機」(Bomber),學校吉祥物是象徵原子彈爆炸的蕈狀雲,保齡球館以原子 (Atomic)命名,所有居民都知道,漢福德製造的武器鈽,用於1945年8月9日投擲長崎的原子彈「胖子」(Fat Man),造成十萬名日本人死亡。里奇蘭鎮民以原子彈為榮,當被外人要求解釋這種黑暗的「自豪感」,他們說:「我們並沒有發動戰爭,我們結束了戰爭。」
然而「他們」或「我們」都不能全稱所有鎮民,小人物自有談論大事件的邏輯,即便只是小小的不安,以及於事無補的懷舊,而我們應該知道,多少突破性的想法,起源僅是小小的不安。導演Lutzig採取古典的傾聽與發問,安排朗誦詩歌、對話討論,把小鎮歷史教師、中學學生、核武工廠員工、罹癌員工家屬都甩回時光洪流裡。她重視所有情緒,讓各種立場的人都有機會表達,剪裁進一幅遠離中心的圖像。
在小鎮高中教歷史一輩子的資深老師,對學校的蕈狀雲吉祥物感到不妥,提議更換,卻被同事誤解為反對美國、反對漢福德工廠,造成失和與反目;社區餐廳裡,漢福德退休員工打牌喝咖啡,其中一位在導演鼓勵下扭捏著尷尬的肢體,竟頌唱起憂傷的地方民謠與詩,感嘆被核工廠汙染的土地、緬懷含辛茹苦的開墾史(在核工廠裡,一個老白男文青!)。當身邊認識一輩子的同事露出驚訝神情,他撇撇嘴說,「除了輻射防護外,我還懂得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也許身處核武製造中心的人,早就對原子彈所承載不成比例的愛國主義與道德矛盾了然與胸,但任何改寫既有故事的念頭,往往須面對社區中的阻礙與嘲弄,多數人選擇把不安藏在心裡。導演在片中始終只以簡單婉約的畫外音現身,邀請受訪者打開心扉,說說傷心與回憶,因為咄咄逼人的扒糞式質問,必然無法引出人的溫柔。
沒有人天生認同仇恨,然而在複雜的世界中,若疏懶理解,恨意就容易滋生。導演Lutzig在訪談中說,「紀錄片是進入一段過程,而不是解答。」我們需要理解的對象是過程,而非得到快速解答。在川普2.0與原爆八十周年的當下看這部片,也許會同時激起警覺與犬儒,以及重新質疑、檢視美國人「可以自在地談論表達各種相左意見」的自豪。紀錄片帶來旁觀者的視野與介入,問出局內人問不出來的問題,在全世界翻天覆地反省美式自由民主之禍的此刻,或許能夠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核電站-300x253.jpg)


-5-1-3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