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的時候,我開始在綠盟的前身「環盟台北分會」負責反對淡海新市鎮築堤造地計劃的組織工作,因緣際會被當時剛改組成立的環盟北海岸分會會長邀請前去幫忙。當時和北海岸人士熟稔的原本是學長陳建志,因為「台北分會」本身的任務分工,淡水和北海岸地區希望由我逐漸接手,而他第一次帶我去拜訪時已是會員大會,會議上被巧妙地宣布為台北分會願意跨區幫忙並請我接任過渡期總幹事。於是那次「吃會」(當時的會長相信,在北海岸這種鄉下地區,在會員向心力仍弱的狀況下,要保證會員大會能辦得起來,就得將開會地點選在餐廳,通常就是邊吃晚餐邊開會),開始了我將近一年奔波於台北—淡水—金山萬里交界的反核地方組織工作。聽起來很酷對嗎? 繼續看下去囉!
當時的環盟北海岸分會剛經過一些內部重組。辦公室位在金山傳統菜市場入口旁的一間舊樓房二樓。這個所謂的辦公室會址,其實就是一個新任會長商借來免租金的空屋,辦公室的窗戶有幾塊沒有玻璃,廁所是與樓下的鎖店共用,而且與其稱為廁所,其實是個非常古老又燈光不足的極小空間,說穿了就只有一個佈滿黑垢,沒有水箱蓋的馬桶座,有點小潔癖的我,只敢偶爾勉強用來小解。也因為沒有窗戶,雖然會長說後面有個房間可以鋪床睡覺,但我不敢睡在那裡(怕蜘蛛、蟑螂,也怕不速之客)。所以在那裡工作的期間,我幾乎都選擇睡在自己的車上,一台躺在後座腳無法伸直的迷你小車。而車子則停在不同地方,有時停在金山老街附近,有時停在停車場,這樣可以臨近公共廁所,以備不時之需和基本盥洗。呼!
那個時候,北海岸地區不像現在,觀光咖啡林立,1996-97的那個時期,從三芝到野柳,只有兩三家還算雅緻的咖啡店或泡沫紅茶店,他們都是我從台北沿著淡水開往金山路途唯一的歇腳處。那個時候,也還沒有現在流行的各種在地觀光節,「嘸發展ㄟ庄腳」是金山與石門人對這裡常用的描述,也隱含他們對核電廠的怨恨。明明距離不到100公里,城市與鄉村的差距感並不小,「台北」還是帶著「中央來的」,「素質較好的」等隱含的強調。似乎就是這樣,會長在北海岸地區介紹我,用得是一種很奇妙的語彙組合,好比說碰到一般民眾就說「伊環保ㄟ啦」(於是有些情境下,當地民眾會誤以為我是縣政府環保局的),碰到當地環保聯盟會員就說「伊台北總會過來支援ㄟ」,碰到知道台北分會的就介紹「總會嘸效啦,要靠一這陣台北分會ㄟ哮年ㄟ」。為此我的外形和角色扮演間就有點「違和感」,那時我一頭馬尾長髮過肩,多半時候襯衫外放又穿牛仔褲。記得有一次和幹部們上山去看一間工廠的山坡地工程是否應該檢舉,老闆對我畢恭畢敬,我當下知道他誤把我當成了環保局的稽查人員,儘管,他手上還捏著我那張台北分會的名片。
那真的是一個刻苦的年代,反核四當時是全國反核運動主要聚焦之地,鹽寮反核自救會也還有很強的動員力,但反觀涵蓋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擁有核一、核二的北海岸地區,即使在1988年左右就開始在地反核遊行,早期更因為發現祕雕魚而聲名大噪,但我去協助時的北海岸分會早已因為內部人事紛擾,飽受「誰暗地裡其實有拿了台電的錢」之類的流言,而互相猜疑,地方頭人間互相攻訐與流言蜚短,形成人際關係上的一大困擾,使得組織運作大不如前。
我一個外地來的年輕人,大概是頂著「台北分會」是「很厲害的搞環保大學生」的光環,變成地方頭人間不好批評的中間人。因為是「外地人」,是「有環保知識的外地人」,所以「咖厲害」、「應該不會拿錢」(聽過最差的評價是,「他台北來的,但是被誰誰誰利用!」)。但也因此面臨會務重整階段,沒有經費,沒有真正的幹部,所以當時的會長才打了這樣方便算盤。我的專職人事費就是這樣七拼八湊起來,一開始是台北分會出四分之一、北海岸分會出四分之一,環保聯盟總會再幫忙出二分之一人事費。而其實台北分會自己的秘書處在那個時候,都常常因為沒有收入而拖欠人事費。總之,就是一個理念:搞運動,領不到薪水也得搞(其實對士氣很傷),即使窮,也不能放著別人不管!而我的任務,就是幫忙把分會組織確立、拜訪地方幹部並協助發掘和訓練當地有潛力的年輕專職。
經歷了地方的風風雨雨,1996年因為蘭嶼核廢料儲存場的抗爭,核廢料運回核電廠重新儲存,引起地方居民的反彈。民眾認為當初接受核電廠已是當地無法逆轉的委屈,但過去一直天真的以為,政府至少有承諾核電廠不會成為核廢料的最終儲存場,如今卻把蘭嶼不收的東西直接又載了回來,豈不是「軟土深掘,吃人夠夠」?於是北海岸分會決議要在5月19日舉辦圍廠抗爭行動,考量到兩座核電廠的入口動線和地方居民參加行動的便利性,選擇以核二廠作為圍廠施壓的象徵性行動。我頭一次背上抗爭指揮的帶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北海岸分會的幹部們一方面擔心動員人數不好看,怕部分幹部放鴿子,讓他們成為地方笑話,另一方面,他們又聽說萬里有另一群居民自主要來加入,但是放話若我們的行動太過溫和,他們不排除衝進廠區,逼迫核二廠方具體切結核廢料遷出時程。而我作為當天行動指揮,也果真見識到底下群眾鼓動著要我們帶頭往前衝破封鎖線。我該怎麼做決定?那年,我23歲,站在宣傳車上,突然覺得整個世界對我放了空,一個禮拜來的勞累與緊繃都斷了開來 …..
這個圍廠抗爭行動,並未在當天的新聞上留下太多時間,在反核運動上也鮮少被記上一筆。或許它仍是值得被記起的,就像其他很多未成為歷史記錄的抗議事件一樣。當「反反核者」看著聚光燈下的反核之眾,嫌惡起裡面的名嘴、明星,嫌惡擁核聲音突然消失,他們或許該知道,擁有龐大資源的台電事業體,霸佔核能正當性舞台三十多年,這些年裡,是多少並不富裕的鄉里小民,必須抗拒台電樂於花錢籠絡的機會,必須貢獻自己的所得,必須忍受被冷言冷語,疑東疑西的流言,才能支撐起反核運動的微弱延續。如果不是因為福島核災讓大家忽然被驚醒,原來都市中產階級的偏安心態,最終會是吞噬子子孫孫命運的助手,反核運動很可能還在沒錢、沒人、沒聲音的窘境下默默經營!一直到現在,我才有機會作為歷史見證者之一,重新把這個歷史故事講述出來。而那些年、那些算不上英雄的一張張反核臉孔,甚至,永遠沒有機會像近日被媒體特意採訪報導,怨嘆專業意見沒有被傾聽的核電廠內工程師,一生裡至少有一次,有尊嚴的分享他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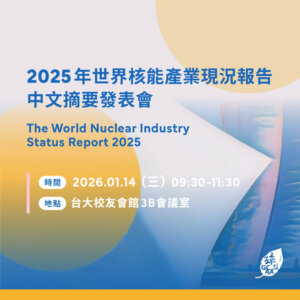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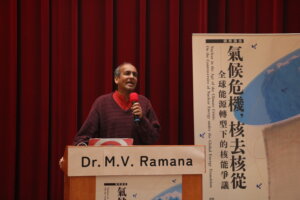


核電站-300x25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