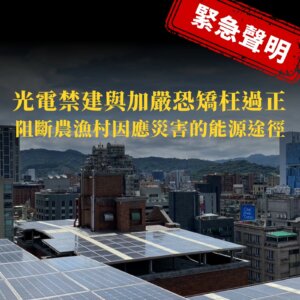《小鎮里奇蘭》(Richland)是一部敏銳作品,該片導演於2024年參與第14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里奇蘭為漢福德廠(Hanford Site)的員工及其家屬所居住的企業樣板小鎮。漢福德廠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它是美國聯邦政府在二戰期間所設置的國防機密設施,在當時為原子彈等級的鈽之製造地。漢福德在戰後則成為核武等級的鈽之製造地。
身兼導演、製片、剪輯師的艾琳.路茲堤克(Irene Lusztig)的政治立場與她關注和相處多年的里奇蘭居民截然不同。她選擇聆聽小鎮不同世代,不同的群體的生命體驗。由於片中對比居民多種敍事,乃至於原爆倖存者後代的觀點,影片並無調查報導的追根究柢,不疾不徐的節奏反倒呈現出一種以鏡頭實踐參與、觀察的風格。
當地居民所思、所見與外界的立場不盡相同。漢福德廠污染的記錄屢見不鮮,該地於1957年和1969年發生大火,核武級的鈽隨著煙塵外洩,造成輻射污染。然而里奇蘭居民和美國原子能委員似乎視而不見輻射污染問題。里奇蘭當地學校的預算,遠高於漢福德處理核廢的費用。
當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1認為,核工業既能製造核武、核電,必然能夠處理核廢。在1970年代之前,核廢料的處理只占原能會年度預算的0.1%。為避免大眾恐懼核廢料,進而影響核武生產、軍備競賽,絕口不談及不處理核武等級高階核廢料問題、才是維持漢福德廠和里奇蘭日常運作的上策。這項政策使得漢福德成為美國境內遭受輻射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
里奇蘭居民和大多數漢福德工人直至日本廣島和長崎原爆後,方才得知包括三位一體原爆試驗和長崎原爆的兩顆原子彈所用的鈽,是在漢福德製造。影片中一位里奇蘭餐車老闆, 同時也是前漢福德工人,坦言摧毀長崎的原子彈之事既不好,也不壞,原爆之於維護美國利益是絕對必要。換言之,他並不反對動用核武。這個立場的前提是自身並非受害者,並且美國動用核武時,可以決戰境外。他的立場與廣島原爆倖存者的第三代Yukiyo Kawano成了鮮明的對比,Kawano既視覺藝術家,也是反核人士。
片中另一個場景則是帶到里奇蘭無所不在的原爆、戰爭意象。當地保齡球館以原子球 (Atomic Bowl)命名。當地街道是以質子巷(proton lance)為名 。小鎮高中橄欖球隊更以轟炸機命名。學校吉祥物則是蕈狀雲,校方和多數教職員對支持戰爭的傳統更是引以為傲。
然而導演呈現這些畫面的目的絕非獵奇。鏡頭接續探索多名小鎮居民的父執輩辛勤工作,帶給全家優渥生活,之後卻因輻射暴露而罹癌早逝。這與影片中工人僅穿著塑膠布衣服在廠區受到輻射體外曝露的歷史畫面相互呼應。至於居住在漢福德下風處的居民則是因輻射暴露,使得許多嬰兒未滿週歲已然夭折,因而有了大片嬰兒墳塚。
《小鎮里奇蘭》有個場景提及「綠色奔跑」(Green Run)活體實驗。美國聯邦政府於 1949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漢福德秘密釋放釋放5,500 至 12,000 居里(即200 至 440 太貝克,或200 至440兆貝克)的碘 131,以監測游離輻射之於人體的影響。換言之,當地居民和下風處者,不分男女老幼皆淪為政府實驗用的白老鼠。
此事使人反思,原爆的戰場和核武競賽是否只在「境外」?原爆是否「既不好,也不壞」?所謂的「維護美國的利益」究竟是指哪個階級的利益?
歷史學者凱特.布朗 (Kate Brown)曾於《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一書指出,里奇蘭是美國社區規劃的烏托邦樣板。為了使工人階級支持核武工業鈽的生產,資產階級既以消費主義和國家大量補貼麻醉工人階級,使其享有優於全美各地的高所得、高消費力,在此同時又以放射物質毒害工人階級。換言之,軍工複合體使當地工人生活優渥、汲汲瀯瀯於眼前的消費者權利,於此同時自動放棄公民權、生物權。當地居民既是順服於體制的加害者,也是體制下的受害者。
本片經由讓小鎮居民並陳各式觀點,進而反思「美國人如何記憶(或遺忘)、面對(或不面對)、處理(或不處理)自身所涉及暴力歷史。《小鎮里奇蘭》在原爆與戰爭敍事,從未出現任何針峰相對的場景。影片細緻、多元的行進方式反而為有意尋思的觀眾留下許多想像空間,值得社會大眾一起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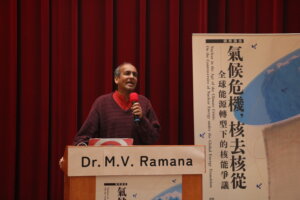

-12-3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