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的經濟發展似乎面臨很大的問題,而以高耗能、高耗水、長工時的傳統產業或電子業代工GDP至上模式,早已面臨巨大的挑戰;但後來以西進前往中國世界工廠,似乎減緩產業發展轉型的壓力,但這資本轉移伴隨著的污染轉移,以及較低勞動成本,也隨著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大環境條件改變,而又成為台灣窒息式發展的困局。而政府提出的因應方法,卻還是想透過更多的鬆綁、特區、自由化,來換取降低成本的商機。但這些也讓人憂心,將讓犧牲環境、勞動條件和不公平的租稅減免,延續「褐色經濟」和「分配不正義」的惡性循環。
再來更大的終究還是「發展路線」以及「區域合作」的問題。台灣過去十年,也經歷了更劇烈的中國崛起、亞洲經濟整合等問題,兩岸、區域環境、經貿問題的糾結正在快速加劇。尤其政府以及企業部門,壟斷了這方面的話語權,形成「台灣唯有經濟發展以防邊緣化」、「社運團體還在扯後腿」的制式印象。從東協加三、兩岸經貿、自由貿易區FTA談判,似乎台灣全民變成「如何讓我們比較好賺錢」的啦啦隊,而忽略了這其中可能的分配正義、社會衝擊、環境與勞工標準倒退、不當補貼特定產業種種社會矛盾。
也因此,在思索台灣未來的環境問題以及發展模式的重要關鍵時刻,我們也希望能夠探索更多促成社會對話、改革運動的不同方法與面向,以及可行的發展路線圖。而這不再是只看GDP數字,而是努力減少實質環境與社會外部真實成本,追求「經濟成長」扣除「付出代價」的「實際社會福祉」,那將是一種「綠色經濟」的思維。
在這樣的願景下,邁向綠色經濟的路線圖中,「企業社會責任」不再是口號,也不是做功德,反而成為企業競爭的引擎。
台灣長期以來的環境運動與公眾監督,政府如果只看成是「找麻煩」,企業看成是「妨礙投資」,那只有更多像日月光廢水污染事件,讓台灣處在用環境代價去換來「褐色經濟」的泥淖裡;反之,NGO的監督,是可以作為創造良好的環境管理的推力,以及轉型為綠色經濟的契機與藍海策略。
在資本流動下,NGO揭露企業不該在不同地方投資有環保「雙重標準」,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和槓桿。所以像台灣迎接台商「鮭魚返鄉」,以及各種資金的流入,不應是鬆綁,而是更嚴謹的管理機制,並且政府應換個思考,讓NGO的監督,成為政府對外談判與促進產業轉型的籌碼。
這其實已不是一種「倡議」,反而是國際社會現實中,越來越多的企業責任規範的現在進行式。對台灣來講,海外環境表現納入企業治理評估機制,遊說企業、證交所、金管會、財政部、經濟部等台灣公私部門,將品牌與其供應鏈的海外環境污染狀況,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評估、重大訊息公開、海外投資核准、投資優惠等企業治理機制的評估指標,可能都是我們應該面對的挑戰。也希望嘗試探索有助於台灣的民間社會摸索出應對東亞以至亞洲經貿整合的另翼主張與應對策略。
上述這些,對台灣環保運動來講,是新且辛苦的挑戰。台灣的環保運動經驗,有豐富的實戰與在地經驗,但總是要求政府出手去監督企業;相反的,中國社會較難挑戰政府,NGO直接監督企業的風險反而較少,卻也開展了不同於台灣的行動與博奕路線。
2008年,我們有機會認識了中國的本土NGO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及其創辦人馬軍主任,當時他們推動的「中國水污染地圖」(搜尋資料庫)還在草創階段,但已引起了很多的關注。而至今七、八年來,除了見證他們發展的變遷過程,以及對中國工業污染制度性以及改善的巨大影響,他們所引領的「綠色選擇」等的戰略規劃與項目推進,也提供了非常重要且具啟發性的經驗。
其實是完全以我們早就耳熟能詳,甚至是有點老掉牙的主張:「資訊公開」、「公眾參與」為核心訴求,但他們所發展出來的思路和作法,卻極具創新性,且一步一步開展,讓企業願意成為一種夥伴關係的可能。
而IPE的經驗,對台灣而言,有兩大部份值得我們進一步認識與作為參考:
1. 環境運動形式與資源的分工整合
台灣環境(社會)運動議題串連是常態,不只領域裡串連,更常跨領域串連,讓運動更多豐富性,且直指更大的結構性問題。在中國,政府對串連有相當的戒心,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從建構工業污染資訊庫彙整開始,拉出「綠色選擇」倡議的綠色消費者概念,包括作為「個人」消費者抵制污染企業,以及「品牌商」選擇綠色供應商(供應鏈)。另外,污染資料以衛星地位標示,必須藉由草根在地團體的在地投入與監督,所以經由「水污染地圖」,把在地、全球產業鏈、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串接起來;再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概念,污染、地域與產業關聯性,找出產業責任;再來由水污染,逐步擴大致空氣污染、廢棄物等污染資料庫,並讓民眾透過智慧手機舉報和關注,成為公眾參與的常態。這裡面包括了面對政府和企業的戰略思考,以及多樣的運動團體、形式與資源投入的分工、整合,是很值得學習參考的面向。
2. 資訊與數據何如成為監督企業與政府的正向工具
去年底的地方選舉大敗,國民黨政府理解「食安風暴」中,資訊不透明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促成了行政院開始推動「開放資訊opendata」,也就是除了以前的資訊公開外,政府還能釋出更多的原始資料(而不只是「整理後」的資料),讓民間社群(社區、NGO、企業、學術研究機構)能比對、生產出更有問題意識或(商業、公益、監督)價值的資料。
如果我們嘗試建構起「企業資訊建構平台」,作為全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包括:台灣環境資訊公開情形、企業污染排放與違規行為資訊公開情形、台資企業在台灣與中國投資相關環境資訊的對接、什麼樣的企業資訊是有助於公眾監督的?等等。而其實這個在「環境」部份,與IPE的倡議剛好全是同樣的概念,所以中國案例反而是很具體的「成品」。

IPE的運動經驗,不是中國環境運動的全部,也有各方不同角度的評價。但其精準的戰略布局和推動的軌跡,提供我們對中國發展趨勢解讀和因應之道的重要觀察視角。另一方面,其獨特且具開創性的作法,也讓很多中國新興的NGO得到啟發,在不同領域以資訊公開角度和角色切入,開展了很多深入且直指核心關鍵的監督,例如環評案件審查制度與實務的缺失,例如焚化爐的排放資訊公開等。
不只是台灣與中國,台灣與其他國家或區域經濟多邊的協議,可能都必須拉出更多跨國管理準則和機制的可能,我們希望設定的標準,都是「比好」而不是「比爛」,不是劣幣逐良幣。而這個逐步建構的過程,是需要很多實務經驗、公眾參與和更多精準的資訊揭露,讓公平、正義的原則得以彰顯。
文 |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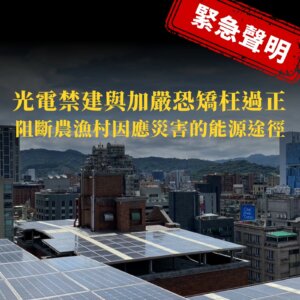



核電站-300x253.jpg)


-5-1-300x200.jpg)